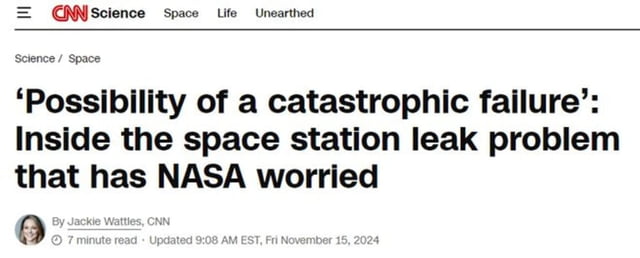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俄國的頂尖大學産生了全世界近25%的菲爾茲獎得主。
科研與教學相結合是俄式教育的一大亮點,也是其能培養出大批非常年輕的頂尖科學家的原因之一。
此外,俄國的科研院所氣氛寬松自由,所謂領導的任務就是制造環境、創造氣氛,使研究人員不受外部環境的幹擾,全力投入到研究中去。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基本照搬了蘇聯的科研教育體系,但我們只抄來了形式,並沒有真正地將如何協調、配合、鼓勵創新的俄國精髓學到手。
俄國的精英教育起源于彼得大帝時代。我們熟知的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包括今日的列賓美術學院等等[1],從建成的第一天起,其目標就很明確,即培養西式精英人才。
這使得俄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裏,在科技、藝術、文化等幾乎各個領域都産生了大量的明星,成爲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和美國拿獎數量相接近的超級大國。
其在昔日帝國時代提出的“我們要向歐洲學習,但我們一定要超越歐洲”的口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俄國青年在各個領域努力成爲精英。
俄國的精英教育基本上學自法國模式,只是它的規模更大、更系統,且目標更明確。俄國人把這一系統用在人文、藝術、體育,乃至科學等各個方面,盡管因爲專業的不同而略有調整,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莫斯科國立大學,創建于1755年,是俄羅斯規模最大的大學。丨圖片來源 :
http://www.msu.ru/en/tour/.
下面筆者將以數學爲例,簡述這一教育系統。對于數學精英,俄國人大致是這樣定義的 :
* 首先,他應該在約22歲時解決一個衆多著名數學家都不能解決的大問題(即證明大定理),並將成果公開發表出來。這個問題/定理有多大,也多少決定了他未來的成就有多大。
* 在30-35歲時,在前面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論,並爲同行接受。
* 在40-45歲,在國際學術界建立自己的學派,有相當數量的跟隨者。
* 培養數學精英,從初中開始
俄國中學、大學的精英教育基本上是爲學生能夠達到第一步而設計的。但同時,它有各類的文化教育、社會教育等等爲後兩步打基礎。
俄羅斯的精英教育始于初中階段。以數學爲例,在學生小學即將畢業時,他們可以從全國公開發行的一本數學物理科普雜志Quant(KBAHT)[2]中得到一份試題。
學生可以把自己做好的試題答案寄到其所在城市的指定部門,再由專家評閱試卷,成績得出之後,城市的指定部門再組織對通過筆試的同學進行口試。
對學生進行口試的人員包括中學教師、大學教授及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被選中的同學將進入所謂的“專業中學”(如果是數學,即數學中學)學習,三年以後初中升高中時,將有一次考試(淘汰),弱者將轉入普通高中。
在莫斯科或聖彼得堡這樣的城市中,一般都有四、五所這種以數學爲主的中學。在這裏,學生們將接受普通的中學教育(包括相當多的文化、藝術以及其它的基本科學知識課程)以完成其人生必備的基本知識,但一半左右的時間將花在數學學習上。
每周他們還有兩個下午去城市少年宮,在這裏,有俄國的頂級數學大師[3],如Andrey Kolmogorov(柯爾莫戈洛夫,1903.4.25-1987.10.20)、Iserale Gelfand(蓋爾範特,1913.9.2-2009.10.5)、Yuri Matiyasevich(馬蒂雅謝維奇,1947.3.2-)等等,爲他們講授數學課。
這些課程的講稿經過整理後也大都會發表在Quant這一類科普性質的數學物理雜志上。這一雜志影響極廣,在歐美世界有著衆多的讀者,包括大學教授、中學老師、學生等。
這種少年宮課程一般都設計得深入淺出,與前沿數學研究中重大問題的提出、現在發展的階段乃至其解決緊密相聯。
爲了讓學生理解並掌握好內容,科學院聯合大學一起爲這一類課程配備了大量的助教,這些助教一般包括大學三年級以上的數學系學生和各級大學教師、科研人員等,並且他們以前也都是畢業于這種數學專業中學的學生,基本上每三位中學生配備一位助教,這特別類似于法國巴黎高師中的輔導員(tutor)。
夏天時,數學中學的同學們還將在老師的帶領下去黑海海濱等地的度假聖地參加夏令營。
在那裏,他們一邊學習提高,一邊玩耍。同時,他們會遇到國內其它城市地區乃至部分外國來的數學中學生,大家可以彼此增進了解,幾年下來,慢慢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圈子[4]。
在夏令營中,還有衆多來教課、輔導的科研人員、大學生、中學老師等等。
筆者認識的許多俄國著名數學家(有的已在上世紀90年代移民西方了)都會在夏天時去這些夏令營輔導學生、認識學生,同時去發現那些有才華、有潛力的中學生,以吸引他們進入數學研究領域。
有些極有才華的中學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高中時就和科學院或大學中的科研人員建立聯系,並進入他們的討論班開始做研究工作的。
因爲這一制度,有許多知名的俄國數學家在18歲上大學一年級時(或在此之前)就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並且將論文發表在國際頂級數學雜志上。
該制度激發了優秀“天才”少年的活力,使他們能有用武之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
俄式教育強調基礎,無論是在科學,還是在體育、表演、藝術等諸多方面都非常出色,這一點也爲中國人所熟知,但它還有我們不了解的另一面,就是更注重實踐。
在數學(乃至大多數科學領域)上就是鼓勵研究、創新,去解決實際問題、大問題。
另一點值得指出的是,數學中學與少年宮、數學夏令營的教育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把中學數學知識、奧林匹克性質的數學競賽技巧、大學各門數學課程的基本數學理念與思想、前沿問題等等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
它使得一小部分學生從高中轉入大學以後,立刻就能進入研究狀態並開始實質性有意義的研究,即攻克著名數學難題。
從高中進入大學以後,這些數學學生中只有少數人能剩下來,繼續作爲潛在的專業數學家被培養。
在我們熟悉的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等部分高校裏,每個學校會有一個由大約三十人組成的“精英”數學班來繼續這部分人的數學學習與研究。
筆者在此想指出,這些大學的數學系中當然還有衆多別的數學學生,但他們的培養方向、要求等各方面都是不一樣的[5],甚至他們將來的畢業文憑都是不一樣的[6]。

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是俄羅斯第一所學術型大學,其曆史可以追溯到1724年,當時由彼得大帝下令創建了科學和藝術學院。丨圖片來源:wikipedia.org.
對于這些所謂的精英學生(乃至一般的普通學生),他們在選課學習上有相當大的自由度。
例如,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可以去科學院的Steklov(斯捷克洛夫)數學研究所的專業討論班中去學習,還可以去別的大學中修習一些本校沒有開設的課程,甚至可以去別的學校(科研院所)選擇自己喜歡的教師的課程等等。
同時,他們也可以在一入大學(甚至在入大學之前),就跟從科學院的研究所中的一些科研人員進行研究、寫論文等。這種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模式是俄式教育的一大亮點,也是爲什麽蘇俄能夠培養出大批非常年輕的科學家的原因之一。
等大學二年級結束時,這三十幾位精英學生的大部分已在學習過程中被淘汰了,只有5-6名能剩下來,此時他們基本都已證明了可以令他們終生爲之驕傲的定理,並開始撰寫論文,且都已將論文發表出來了。
他們活躍在名師的討論班裏,向著新的目標前進。他們的前程在此時也已基本上根據這時的成就而多少確定下來,即成爲研究型的數學工作者。
筆者想在此指出,在俄國研究型大學的數學系中,有相當數量的課程供學生自由選擇,絕非像我們的學校那樣強迫學生去學那些必修課、限制性選修課乃至公共課[7]。
而許多做出過好的科研工作的數學學生甚至可以免掉大部分的課程,以保證他們在黃金創造期間不停地去深入研究學術。許多俄國大數學家是在副博士畢業以後留校任教期間通過教書來學習普通大學生必須掌握的數學知識的[8]。
* 攻克難題,成爲精英的關鍵一步
在俄制大學中,被選入精英小組的學生在二年級下半學年(第二學期)將按要求在一個學期左右的時間內完成他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對數學而言,這篇論文的結果必須是解決學科中的某個重要公開問題,而回顧、綜述之類的論文是不允許的。
論文成績的好壞也基本上決定了該學生的學術前途,即是否能進入科學院的頂級研究所成爲研究人員,或進入俄國頂級大學成爲教師,等等。
值得強調的是,在俄式數學精英教育體制中,要求學生(或未來的精英數學家)必須在22歲左右公開發表論文正是由這一在二年級下半學年結束時寫出論文的措施決定的。該措施能夠得以施行,對老師、學生的質量都有相當高的要求[9]。
這裏例子有很多,比如Kolmogorov將希爾伯特第13號問題給了Arnold(阿諾德,1937.6.12-2010.6.3,曾獲克拉福德獎、沃爾夫獎),Sergey Maslov將希爾伯特第10號問題給了Yuri Matiyasevich等等。
解決這類數學問題本身是任何一位數學家都想得到的榮譽,我們完全可以相信Kolmogorov和Sergey Maslov本人對如何解答希爾伯特第13號、第10號問題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他們對自己的學生的數學能力有著相當的了解,故此可以直接了當將問題告訴學生。
對學生而言,拿到這類問題之後的前途基本上有兩種 :一是把前人有關該問題的部分結果作些修補,再添些新的部分結果;二是直接了當地將問題徹底解決掉。
選擇後者的學生很難從老師那裏得到真正“具體”的幫助,因爲老師也不可能知道答案,但作爲老師,他知道前人失敗的教訓,知道問題難在哪裏,爲什麽有些路走不通(或者可能走得通,但在什麽地方必須克服什麽樣的困難)。
更重要的是,這些偉大的數學導師們作爲國際數學家核心圈子的成員,他們對問題是否到了該被解決的時刻本身有著敏銳的的洞察力與基本直覺,這一點對圈外的人而言是很難覺察到的。故此他們可以在對學生有相當了解的情況下將問題在合適的時機告訴某個學生,並期望他(她)能成功地解決問題[10]。

Andrey Kolmogorov,俄國著名數學家,其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對概率論公理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丨圖片來源:http://kolmogorov.com/.
對于精英小組的學生們而言,二年級下半學年的論文選題是他們步入學術界最關鍵的幾步之一。可以說,他們爲此已經作了多年的准備。
此時,他們要在自己諸多非常熟悉的老師們當中選擇一位作爲自己今後多年的導師。
一般來說,每個學生會在聽課、討論班以及私下接觸的基礎上先去和三位(有時甚至是四位)老師進行接觸,慎重考慮他們給出的研究問題,並同時要考慮多種其它因素,如自己是否願意和某位老師長期共事,大家性格是否合得來等等。
當然,學生此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興趣,然後是從老師那裏得到的題目的難度,以及自己有多少把握等等。但老師的非學術因素,如人品、性格、愛好,在此時也對學生的選擇起著重要作用。
在經過極其慎重的考慮之後,學生最終自己作出最後的決定。對于一位18-19歲的青年人來說,這一選擇並不容易。
其實,在俄國的知識分子家庭(或世家)中,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許多時候學生父母的意見是很重要的。有的時候,學生也會聽取他本人從中學時形成的那個精英學生圈子內的“學生長輩”或是他(她)曾經的tutor(輔導員)們的意見。
選擇什麽樣的題目、進入什麽樣的領域或哪一個分支等等,這些對學生來說,有時候是很難把握的。尤其對于某個學科將來的走向,或者某些新興學科的前途,學生不僅要經過慎重思考,許多時候也不得不多方咨詢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另一方面,有的學生不僅志向高遠,而且有極其超常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欲望,他們會選擇最艱難的著名問題,如我們前面提到的Arnold、Matiyasevich等人。但我們必須指出,這種選擇是有其冒險性的,我們知道的只是成功者的姓名。
筆者遇到過一些失敗者,他們早已被普通人忘記了,只有他們過去的同學或曾經的學生們還記得甚至欣賞他們的才華和勇氣。
盡管對某些人來說,俄國精英教育機制是殘酷的,但無可否認,這一制度産生了大量的年輕精英人才,成就了上世紀蘇聯科學界一個群星燦爛的時代。
* 研究所與大學合力,保障精英教育
在拿到副博士學位以後,俄國的科學家們開始進入大學或研究所“正式”工作。與法國一樣,如果他們要拿到相當于大學教授的高級職位,必須要再繼續努力,寫出所謂的“科學博士”論文。
需要指出的是,俄國的科學博士論文水平極高,如果不是解決行業中的頂尖大問題(從數學上講,應是拿到菲爾茲獎級別的工作),則必須是建立理論體系的大工程。
以數學爲例,美國數學學會專門組織專家將所有俄國數學方面的科學博士論文翻譯成英文,可見對它的重視程度,同時,也是對俄國數學的尊敬[11]。
* 俄國的大學與科研院所是一個大型的系統工程,爲俄國精英在畢業以後的發展,也爲年輕精英的培養提供了舞台、條件以及各種職業上的保障。
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時從蘇聯基本照搬了俄國模式,但是,我們只抄來了形式,並沒有真正地將如何協調、配合、鼓勵創新的精髓學到。
在俄國的主要高等教育發達城市(如莫斯科、聖彼得堡、新西伯利亞、喀山等)中,都有大學(包括綜合性大學、師範類院校、理工大學以及各類更專業的工科、文科、藝術院校)以及一些科學院的研究所。
大學擔負著教學任務,而各種研究所是科研潮流與時尚的引領者。
俄國大學中的許多老師一般都在研究所中擔任一定的正式職位(有半職的,有四分之一職的),在完成教學任務以後,他們都主動去研究所參加各種科研活動,並輔導在所裏學習、研究的年輕學生們。
這一辦法使得研究所裏的教師和大學裏的學生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聖彼得堡大學的數學老師可以通過Steklov研究所來正式輔導聖彼得堡師範大學的數學學生寫作論文,指導其進行研究;Steklov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可以指導俄國各大學的數學系學生進行論文寫作、研究,這樣可以使有限的教師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與利用。
從另一方面講,科學院的研究所裏的科研人員大都會在當地的大學中兼職授課,有的資深學術大師同時還是大學裏的教研室主任,通過教學(包括對大學教師的直接影響、接觸等)來傳授他們的學術見解與理念。
通過在大學中教課,他們也可以及時發現有潛力的學生,將他們及早地吸收到科研隊伍中來。
與此同時,研究所本身還舉辦各種討論班、演講、系列課程等,這些活動大都安排在下午5:00以後,使得周邊的大學、中學的專業教師和有興趣的學生能夠找到時間來參加這些活動,爲他們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創造機會。研究所與大學既競爭又合作的互動關系是我們當年沒能從蘇聯學到的東西[12]。
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向蘇聯學習,照搬照抄了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將蘇聯的教材、課程設置等一律搬過來。然而,我們好像沒有學到俄式教育的靈魂[13]。
其實,俄國大學盡管設置了這些課程,用的教材我們也曾用過,但如何教、怎麽教才是最關鍵的。比如在聖彼得堡大學,學生的基礎課都是由一流的有過輝煌科研成果的資深教授來講授的(比如邏輯入門課常常由Yuri Matiyasevich講授,幾何介紹由Yuri Burago(布萊格)講授,傳統分析由Sergey Kisliyakov講授等)。
他們在講授這些大學入門課時,也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結合著當代的研究潮流與最新成果一起來講授。同時,他們在講課時對所講的內容不時作出判斷、評價,並指出新的研究問題,這才是課程真正的精彩之處,這些也是課程的核心和靈魂。
對于書上的內容,學生自己要花時間去讀去想,每門課程還配有習題課,習題課的老師一般是中年或青年教師,他們在專業研究領域極其活躍,具有過硬的專業技術,同時也願意花大量的時間與學生去想一些艱難的技術問題。
在學習正常基礎課的同時,學生可以自由地去修習各種討論班。在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這些頂級學校的數學系中,各種專業的數學討論班每年有不下一百個,爲學生提供了豐富的選擇[14]。
正是這種自由的學術空氣激發著年輕學生的熱情,同時,也爲教師的科研提供著動力。
無論是在科學院還是大學,教課或領導研究的老師要對學生(尤其是精英學生)有足夠的了解,即對他們的科研潛力、興趣等都要有正確的估計。
如前所述,俄國學生如果要進入職業數學家的圈子,就必須在22歲左右拿下大問題(這個問題一定是行業內的著名難題,且被別的名家試過而沒被做出來的)。
學生固然要戰勝挑戰,但老師在這裏的作用(包括選題等)是必不可少的,如何指導學生達到這一步,對老師的智慧也是極大的挑戰。
而在另一方面,大學與科研院所也要在制度上提供各種保障。
盡管我們看每位成功的俄國數學家(科學家)好像各有各的故事,有些人甚至還常常與領導發生各類沖突,但總的來說,俄國的科研院所是相當寬松自由的,而科研院所的所謂領導們的任務就是制造環境、創造氣氛,使研究人員不受外部環境的幹擾,全力投入到研究中去。
以著名的Steklov研究所爲例,該所五年才考核一次,常有人五年什麽成果也沒有,甚至十年過去了還沒有,如果一個研究人員十年沒有一篇論文,他/她也只不過到所長那裏去解釋一下,他/她在這段時間裏到底在做什麽,思考什麽問題,遇到了什麽困難等等。
據說Steklov研究所還沒有出過一個一事無成的研究人員,如果有什麽人寫的文章不多,他必定是做出了可以載入史冊的工作(如Yuri Matiyasevich、S. Adian、G. Perelman),或者他培養出了一群星光燦爛的學生(如Yuri Burago)。
不難看出,源于前蘇聯的俄式精英教育系統要遠遠比法國的複雜,並且它是一個牽涉到中學、大學、科學院乃至許多政府職能部門的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它的投入以及對各種人力資源的調用是相當巨大的。
如果我們要學習這一系統,不可能是某個大學、某個地方(大概除北京以外)可以去仿效的。盡管我們在建國初期模仿了蘇聯的教育系統、科研院所模式,但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積聚起如此大量的高級人力資源。
所以,我們能做的也只能是像美國或其它歐洲國家,如英、法、德乃至日本那樣,以各種方式引進其高端人力資源爲我們的科研和教學服務。
注釋 : [1] 俄國在彼得大帝改革之時,早就有著自己的文化傳統,然而彼得大帝的改革是要將俄國拉向西方,建立大學也是爲了培養西式人才。
俄國大學(如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等)從一開始就與舊的俄國傳統文化無關,而且從一開始,就定位在培養頂級精英人才。
在學生來源上也是這樣,甯缺勿濫。據筆者所知,聖彼得堡大學剛開始創辦時,學生的人數少得可憐,只有7人。但同時,爲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學校的大門又是向全社會敞開的,即便是農奴,只要有才,也可以進入大學學習,並得到各類資助而成爲大師。
例如,18-19世紀的Andrey Veronikin就是一位農奴出身,最終因其在建築、藝術等多方面的成就而被選爲俄羅斯科學院的院士,成爲永垂史冊的人物。
類似的例子很多,這是筆者知道的最典型的一例。從大學創建之初直至今日,對傳統俄國文化的學習仍在繼續,但大學等當時的新生事物建立在聖彼得堡,所以新、舊兩種教育體系基本相安無事,但切割得很清楚,沒有利益上的沖突。
新的大學盡管起步艱難,但最後終于成爲主流,成爲俄國乃至世界科學文化明星的搖籃。
[2] 這是一份創立于1970年的,以數學和物理爲主要專業的科普雜志,其對象是普通大衆和學生。該雜志在俄國、歐美都有衆多讀者。
[3] 俄國的頂級數學大師也是世界的頂級數學大師。
[4] 這一圈子可以說對他們終身都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在學術職業生涯上的互相幫助等方面。
[5] 他們的培養方式有些類似于我們五十年代從蘇聯學到的那一套比較正規的、嚴格的數學教育。
如今這套教育在中國已經大大縮了水,原因是我們大學的數學系不斷擴招,且九十年代以後又開始向美國學習其大衆教育模式,所以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的數學教育完全就不是爲了打造精英而設置的。
[6] 蘇俄的大學文憑(Diploma)相當于美國或中國的碩士,有普通文憑和紅色文憑兩種,極少數優秀學生能拿到紅色文憑。
[7] 我們的學校應該學著尊重學生的選擇,而不是強迫他們接受學校的安排。
筆者在美國的Rutgers大學哲學系念書時,在數學系、語言學系、心理學系、計算機系乃至藝術史系都修習過研究生課程,從來沒覺得Rutgers大學強迫我學過任何一門課程。
我們國內的許多做法(如學校的課程安排、教學管理等等)是爲了便于外行進行管理,而不是爲了培養人才而設立的。
[8] 其實,許多歐美頂級大學都有類似的情況。例如筆者的博士導師Simon Thomas在倫敦大學博士畢業以後還沒學過“泛函分析”課,那時他才23歲,已解決了簡單群分類這一重要問題,並因此拿到了耶魯大學的教職。
[9] 這裏所說的精英學生在第二學年下半年用一學期左右完成第一篇學術論文,在完成論文的時間長短方面是有一定彈性的,有時爲了徹底解決一個大問題,會拖上一兩年的時間。
這一時間尺度基本上由學生的導師和他(她)所在的研究室主任來把握,如果時間過長,導師與研究室主任將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壓力。
例如筆者曾經聽到著名的邏輯學家Shanin(沙甯)講起過Yuri Matiyasevich用了近兩年的時間才解決了希爾伯特第10問題。
在接近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時刻,大學乃至研究所裏的行政人員開始不停地找Shanin談話,希望Matiyasevich拿出“應有”的成果。
對于Shanin來說,這種壓力是巨大的,他不得不要求Matiyasevich找一些在解決希爾伯特第10問題之前所做的小結果以應付來自各方的壓力。
但同時,Shanin覺得Matiyasevich絕對有希望拿下希爾伯特第10問題,因此盡全力保護Matiyasevich,使他能夠不受干擾並最終將問題解決掉。
在精英教育中,對導師乃至導師的上級領導的素質都有著很高的要求,如何協調行政與科研教學的關系是我們的大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要發展精英教育,這一點則更爲重要。
[10] 筆者這樣寫,也許多少有些唯心論的味道,但在數學界,許多大問題在解決之前的確是有先兆的,而這種先兆可以多少被圈內的大數學家(們)覺察到(只不過這些大數學家本人在該問題上已是“江郎才盡”,沒有什麽新主意、新思想去克服解決該問題所要面臨的諸多困難)。
我們可以舉幾個現成的例子。美國數學家Martin Davis(馬丁·戴維斯)在上世紀60年代末即感覺到希爾伯特第10問題應該快被解決了,他甚至有直覺這一問題可能會被一位極年輕的俄國數學家解決,他唯一沒猜到的是Yuri Matiyasevich的名字。
群論中的Burnside問題被俄國數學家Peter Novikov和他的學生Sergey Adian及英國數學家共同猜到,而最終由Peter Novikov和Sergey Adian聯合解決的。
在50年代初期,20世紀最偉大的邏輯學家K.Godel(哥德爾)就已模模糊糊地猜到了喬治·康托的連續統假設(即希爾伯特第1號問題)的獨立性,並爲此寫了一篇結合數學和哲學的頗具科普色彩的文章來闡釋他的觀點。
最後這一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年輕的Paul Cohen在發明了新的數學工具--力迫法的基礎上將其解決。
在我國吵得沸沸揚揚的龐加萊猜想(Poincaré Conjecture),丘成桐、Hamilton(漢密爾頓)等人都猜到了它有可能將被解決掉,最後由俄羅斯聖彼得堡的G. Perelman(佩雷爾曼)將其成功解決。
[11] 其實,美國數學學會、倫敦數學學會聯合起來,將俄國幾乎所有的知名綜合數學雜志以及衆多的專業數學雜志一字不漏地全部翻譯成英文,這本身就說明問題。
同時,大量的俄國教科書被翻譯成英文等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並應用,也說明了人們對這一教育、科研體系的認可。
[12] 如何發展大學與科學院下屬研究院所的功能,使之更有效地聯合起來爲培養中國高端人才作出實質貢獻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嚴肅而且緊迫的課題。
[13] 筆者想指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俄國的頂尖大學(如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新西伯利亞大學等)産生了全世界近25%的菲爾茲獎得主,每個大學都有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不包括文學獎、和平獎)。
[14] 當然,我們不得不看到,能夠組織如此衆多的討論班需要學校本身擁有衆多的人才,這些人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們的科研事業(外加部分組織工作)中。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衆號“賽先生”。---[撰文 : 張羿*編輯 : 潘穎/來源 : 返樸]